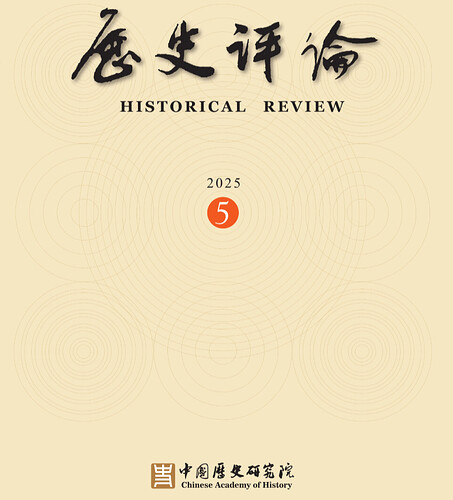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中修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多么的腐朽,已经烂到需要将乡贤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抬出来维持自己的继续统治。所谓的什么乡贤不过是中修的基层打手罢了,它的本质就是农村的统治阶级,中修把乡贤包装成什么调解矛盾、做公益的人畜无害模样,实则在无产阶级身上又加上一圈枷锁。
2、资产阶级的理论研究是为了指导其实践的,这反动机关历史研究院挖出来乡约乡贤这样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反动制度推广,无非是想用这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拿着这些律令、和儒家反动思想去控制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无权乖乖的听统治阶级的话,无产阶级不需要为这些统治阶级立传,颂扬他们的“功德”,无产阶级要自己有权,打破枷锁,所以需要先锋队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11月8日,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历史评论”杂志发布了一篇文章名叫“乡约助力明清基层社会治理”,这个字眼似乎十分熟悉,中修在近年来也推出了所谓“乡贤制度”的农村治理制度,这两者似乎非常相似,今天就让我们探究一下它们的真面目。
一、乡约乡贤制度的概念
首先要科普一下乡贤,这是由过去在基层农村社会中具有威望和影响力的精英人物,包括士绅,地主,宗族领袖等,说白了就是为中国地主阶级看门守院的奴仆。至于乡约一般是由乡贤制定和维护的农村管理模式,就像这位研究员所说:
“乡约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广泛存在的契约性社会组织,要求参与者通过自省互助、劝善规过,以实现“一道德以同俗”的理想。乡约在北宋熙宁年间由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创设于陕西蓝田,在南宋经朱熹补益,后以《增损吕氏乡约》流行。明清时期,乡约在华南、华中和华北等地得到推广,呈现出宗族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在晚清成为服务地方政府的职役。明清两代是乡约发展的鼎盛时期,乡约以道德礼义为原则,通过制定面向全体成员的约束机制,促进地方治理体系完善。乡约还影响当时的社仓、义学、家风建设,甚至协助维护地方治安,对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已经把乡贤和乡约的性质说清楚了。在过去的王权社会,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统治者管理的稀松,中央王朝的管理无法完全触摸到基层农村,也就是“王权不下乡”。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占中国大地多数的农村无法管理怎么办?朱熹这个统治阶级的思想爪牙便提出了妙计,那就要和农村本地里的势力家族合作,扶植他们来管理农村。这些势力代表了中央王朝和基层农村之间的联络桥,利用“道德礼义”来约束农民,让他们接触儒家的“畏天,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圣人思想”,老老实实的守着自己的地给皇帝和地主交税交租,不许违抗封建制度。那要是学习陈胜吴广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怎么办?不要紧!还有乡贤来“协助维护地方治安”。可以说乡贤乡约在那个地主阶级专政阶级矛盾激烈的时期,对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可是出力不小,不知有多少自发不满的农民在起义惊动官府军之前就被乡约掐死在史书记载之外了!
那么在21世纪的中国,中修为什么要旧制重启,历史研究院的先生们为什么要重新提起这一制度?实际上和封建时期是一样的。自中修复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发展被掐断,封建势力和资本重新在农村冒出头来,农村人民自然不会甘心自己被剥削压迫,于是开始进行了大到集会游行小到千里上访的软硬两方面的反抗。中修对这种反抗是不能容忍的,但是虽然现在生产力发展使管理范围增加了,但他们自己的落后性和中国地域的广大使他们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管理,于是从封建博物馆中掏出了乡贤制度,从农村中挑选顺应中修统治比较积极的“先进典型”来扶植成为新乡贤,给他们发福利和官职,暗地中纵容他们对农村人民可能的为非作歹,两者相结合,好不快活。
二、乡约在古代起到过的作用
我们回到研究院先生的文章中来,看看他对于乡约的描述。
明清时期,乡约普遍以《吕氏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基本原则。“德业相劝”和“患难相恤”体现《论语·里仁》对“仁”的强调。孔子说“里仁为美”,希望住在有仁者的地方,表达了对美好道德风尚的追求。乡约的推行目的和实践原则,与孔子主张一致,只是为了便于施行乡里,以朗朗上口的言辞改述经典,令百姓易诵易懂。
在推销愚民思想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没有哪个思想比儒家更有影响力、更有毒害性了。孔丘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腐朽的奴隶制和新生封建制的冲突时期推出了儒家思想,为奴隶制站台,本来在秦始皇终结中国奴隶制历史之后被打倒了的,后来汉朝时期封建制度失去自己的先进性之后又被汉朝皇帝捡了回来,修正之后用来维持自己的封建制度。孔丘自己就是十分反对人民运动起义的,他管起义奴隶柳下跖叫成“盗跖”,他后世弟子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统治阶级辩护说剥削压迫有理的道一万年不变;再往后朱熹则直接亲自上阵,推出乡约的概念;王守仁也推动了乡约的发展,在自己做地方官的时候制定了“南赣乡约”,说人民要~~“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就是要李自成张献忠好好当良民。而中修自80年代以来也是一直推崇儒家,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复的强调“弘扬儒家经典文化”,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对中修“仁厚”,对身边自发不满的人“恶相告诫”,让人民不要起来造反。中央号了令,历史研究院先生也就配合作战,在自己的文中大肆鼓吹儒家学问,如果同志们有时间去看看原文就会发现原文真是充满了腐儒的臭气!
明清时期,乡约的组织架构较为稳定,包括年高德劭的约正、约副等首领,以及能秉公录事的约讲、约赞等人员……入约后,参约者需要遵守条规,服从约正、约副教导管束,定期参加讲约,行善有奖、为过受罚,登记入簿,公之于众。
这就彰显了乡约的另一个作用:“维系伦理关系(这是他的用词,我看应该换成维系封建家长制)”。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早就提过: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
这个所谓“伦理关系”就是族权。族权在过去的封建时期的农村是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说皇帝在天边,族长在眼前。族权是束缚农民的极大的绳索,在宗族中,长辈或强宗霸占弱者土地,设立私刑残酷欺压百姓,吸收民脂民膏建立祠堂和院落,对女性、后辈的规训极其严苛,几千年的罪状可谓是罄竹难书。这种封建时期的旧垃圾,中修为了巩固统治,让底层人民如同过去敬畏族长那样敬畏中修基层政府和代理人,竟然试图将封建家长制洗白!
明清时期,乡约在推行思想教化、建构伦理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乡约在发展中与其他社会组织结合,官方色彩逐渐加强,进一步提高国家的基层治理能力。当然,乡约亦有局限。乡约所奉行的理学思想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封建统治是其根本任务。在实施过程中,当主持乡约者德性不端、行事不公,甚至从中渔利时,必然会对乡里秩序造成破坏。
历史研究院的先生终于觉得自己讲的实在是太荒唐了,在最后试图用一点“局限性”来挽回自己文章的一点合理性。殊不知这点挽回颜面的话继续透露着他的反动。“当主持乡约者德性不端、行事不公,甚至从中渔利时,必然会对乡里秩序造成破坏”,他甚至不愿意说乡约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只是扭扭捏捏的说“制度是好的,但是有人执行坏了”,也是,他们的主子还要拿乡约管理压迫农村人民呢,怎么能直接说是封建垃圾呢?只敢说这种话来提醒:切勿选德行不端行事不公的人当乡贤!要挑海瑞、武训这样一心为民的!于是他的主子听从了自己御用反对派的话,搞了一次又一次的基层整风,把黄文秀这样的“好官”推成榜样来。“百姓谁不爱好官”嘛!殊不知在私有制下哪里有好官坏官之分!只有维护统治者的爪牙!
总结
中修前脚推出控制农村的乡贤制度,后脚历史研究院的先生们就一头扎进古书堆里,找了如此之多的资料,写出了如此之垃圾的文章来,给他们的主子做背书。对于这种文章我们可以借用姚文元同志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来做总结:
请读读邓拓这段话吧:“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万钟、米汉雯)以适当的地位。”“过去”,是封建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照例”是“照”地主乡绅特别是恶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乡贤”的统统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要“我们现在”为这批“乡贤”立传,就是要把土改以来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来,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乡贤”的牛马!这不是猖獗得无法无天了吗?响应主将的号召,《三家村札记》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为军阀、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传。
-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连起来了,全部连起来了。孔子,朱熹,邓拓,中修,几百年的乡贤体系,一切都在这篇文章中被串联起来,编成一条千百年剥削压迫人民的铁链,企图锁起一切人民的反抗,让自己的统治江山永固。但是自古而来的人民从来就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现代的无产阶级要用全国一盘棋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链条,在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和自觉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生活中推翻中修,用革命的链条扯断反革命的链条!将一切帝修反遗留下来的封建、资本垃圾统统丢进焚化炉,让统治阶级永远不能拿来维护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