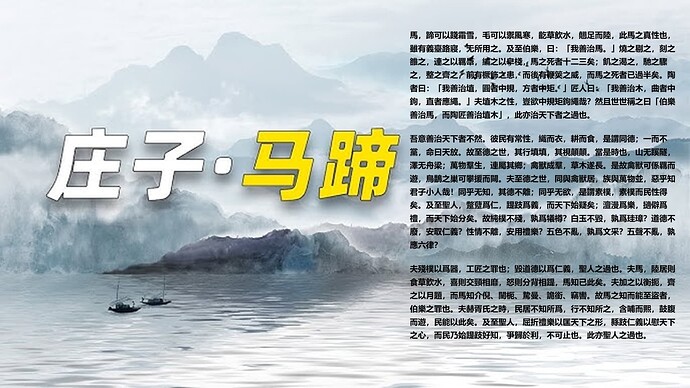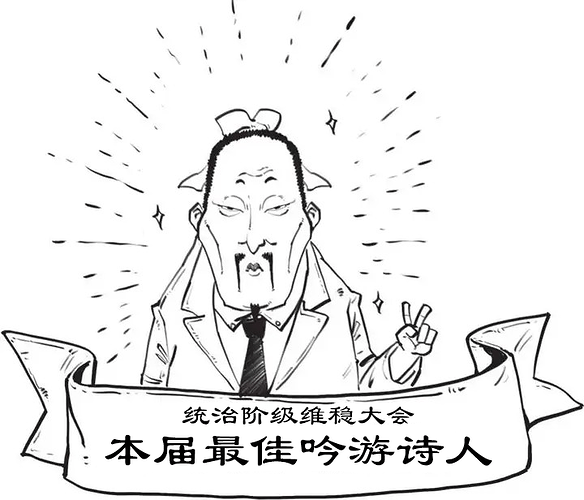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庄子要逍遥,文革时期也有一派人脱离阶级斗争,自称逍遥派,这一派人也就是放弃阶级斗争,逃向了个人主义,远离轰轰烈烈的革命,躲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古往今来的逍遥派,都是不要斗争的,只讲究个人的解放,不管是中国的陶渊明,还是写《瓦尔登湖》的梭罗,他们在经济上都是富足独立的,正因为他们脱离群众,不需要通过革命才能改变自身的处境,只需要远离城市就能改变,所以他们的哲学注定是小资产阶级的哲学,注定是走在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对立面。
2、庄子所谓的反权威放在当代,实际上就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不彻底性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所谓的“顺其自然”也就是顺应、保留现存的统治制度。中修如今把庄子捧上“国学智慧”的宝座,看中的正是其中可以用来麻痹革命精神的——口头上反压迫行动上逃避斗争的自我安慰。灰尘不扫他自己不会走,对剥削制度不去斗争不去革命,令人愤恨的压迫剥削也不会“自然”自行的消灭。
《庄子·外篇》中的《马蹄》是一篇极具思想性和讽刺意味的文章,通过讲述马的自然本性与人类对马的改造之间的矛盾,来批判人为干预自然、破坏天性的行为。
《庄子·外篇·马蹄》(节选)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使之服重致远,劳其筋骨,齐其毛色,毁其真性,以应马政,是故马有死者。
庄子认为,伯乐对马非贵人也。马本有其天性,能够自然生存,无需人为干预。然而人类却把马圈起来、给它戴上辔头、用鞭子抽打它、把它训练得“整整齐齐”,结果反而伤害了马的本性。在庄子看来,这是“有道之人不为也”的事情。庄子用这一类比来批判当时社会各种对人的压抑和人为制度的强制。
但是这样一种“反抗”的思想居然被中修来加以宣扬,捧上国学经典文化,这么看来就有些不对劲了。其实不用猜就知道这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庄子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根本的对立性
庄子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动荡时期,战国的社会秩序崩塌、战争频发、礼乐制度解体。他本人出身寒微,据史料记载是“漆园吏”,是个社会底层的小官吏。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对社会秩序的批判立场具有一定程度的下层视角,他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对强权、对礼法制度、对暴政的反叛和逃避。
他在《马蹄》中批判对“马的真性”的压制,其实也隐喻了“人之真性”被政权制度束缚”的批判。他反对礼法名教,反对帝王霸主,反对战乱与强制规范,这些在形式上具有反权威、反压迫的色彩,甚至与无产阶级的反抗精神在某种情感和文化层面有“相通之处”
但庄子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代表。为什么?
庄子所提出的“自然”思想表面上它似乎是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反对过度的社会规范与制度的束缚。然而仔细分析其深层含义,就能发现它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对立,甚至是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反抗精神的背离。
庄子主张的“无为”和“顺其自然”认为人应当顺应自然法则,避免人为的社会干预。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反历史、反进步的,否定了有组织的社会变革,他不光是反对制度,也反对变革制度。他不是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而是主张“逍遥游”要人“远离权力中心”、自保性命隐居避世,这是一种逃避历史责任的思想。但我们知道,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动力正是基于历史的进步性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历史的前进不是简单地回归“自然”的原始状态,而是通过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通过革命的力量,实现剥削阶级的摧毁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庄子的“自然”思想在本质上否定了历史的进程,忽视了阶级压迫的现实。而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则要求我们通过建立阶级专政,改造自然界与社会结构,推动历史不断进步。
庄子主张“无为而治”,即通过撤除外在的制度和人为的压迫,让事物按照自然的方式自发地发展。他认为任何人为的强制、压制都会导致混乱和不和谐。所谓“无为而治”背后隐藏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对统治秩序的放任自流,甚至是一种对现状的隐性支持。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之一恰恰是“有为而治”。我们不期待“自然”顺其自发地带来社会变革,而是要通过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来改变社会的现状。庄子反对一切人为秩序,而无产阶级恰恰要建立自己的历史秩序,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掌握政权、发动暴力革命,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种历史使命感与庄子追求的“齐物论”“万物平等”“无君无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庄子是幻想着取消阶级,而无产阶级要在先锋队的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直至消灭阶级,这是路径与方法的根本对立。
庄子的“自然”思想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强调“随顺天命”而非主动改变社会现实,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消极性,它主张人应当接受现状,而不是通过主动的革命实践去改变现状。对于无产阶级而言,革命的动力正来自于对现状的深刻不满和对剥削阶级制度的反抗。无产阶级的革命不是“顺应”现有社会的流动,而是要改变这种社会关系,打破剥削与压迫的框架,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具备革命性主动性,要求人民群众要有改变现状的决心和力量,去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庄子思想的广泛传播只会严重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导致对压迫现状的容忍和自我麻痹。
为什么行使剥削的统治阶级会选择庄子的思想来加以宣传?
庄子看似批判权威宣扬“反抗精神”,事实上却否定一切组织与斗争。庄子的“反权威”不是为了推翻统治阶级,而是为了“避世隐居”、“无为而治”,是虚无主义式的批判,是在逃避现实。这就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化斗争从根本上相对立了。对统治阶级来说这种“温顺的批判者”最安全——既宣泄了人民对压迫的不满,又不会造成真正的组织化革命。庄子的思想是可以被转化为“顺其自然”“别去斗争”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打着“传统文化”“国学智慧”的旗号,将庄子的思想包装成一种“人生哲学”,实则是宣扬犬儒主义、宣扬宿命论和反斗争精神,这是对被压迫群众的一种精神麻醉,目的是切断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阶级自觉性。
庄子否定的人为制度是可以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组织与革命的,他的“自然”思想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着深度的契合,赵修官僚资产阶级文化的主流思想将庄子的“自然”哲学推崇为“精神解放”的代表,实际上是在为现有体制的稳定辩护。他们在庄子的思想中看到了一种能够消解阶级矛盾、消除人民反抗的思想工具。因此,他们极力的宣传庄子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还将其作为一种能够削弱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思想资源。这种思想表面上看似讲求个人自由,但实际上是放弃社会改造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令人麻痹的精神毒品。这种思想正好契合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通过推崇“顺其自然”的理念,使工人阶级及其他被压迫者放弃积极的社会改革和阶级斗争。
今天统治阶级把庄子的“反抗精神”拿出来讲,却丝毫不敢讲列宁的组织起来,不敢讲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只会挑选那些对体制批判但不构成现实威胁的“异端思想”来中和阶级对立。制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维系统治的工具,是被压迫阶级组织斗争的武器!庄子把制度当成敌人,却不去识别制度背后的阶级属性,庄子把管制当成枷锁,却不去动摇管制者的根基,这正是庄子思想的危险本质——他要受压迫者躲避暴政,而不是组织起推翻暴政。这样的伪批判当然备受统治阶级的喜爱。
他们说庄子是反抗者,我们说庄子是犬儒者;他们说庄子是批判者,我们说庄子是顺从者。
文化斗争的实质:谁在解释、谁在领导、谁在掌握文化的解释权?
毛主席早就说过: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战线的斗争。”
所以只要国家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只要统治者还是中修官僚资产阶级,那么就不会宣扬出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思想,就只能被迫接受资产阶级的愚民统治。文化不仅仅是人们的艺术、文学或思想表达,它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世界观。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常常成为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其利益和权力的工具,所以文化斗争的实质,实际上就是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文化领域的领导和统治。
所以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能拥有属于无产阶级的正确思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转移,更重要的是进行全面的思想解放,摧毁资产阶级的文化堡垒。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带来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政治权力的掌握,更是对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领导和专政。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确保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确保革命意识形态能够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并最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
无疑是利用政治报路线来搭建起来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家组织。利用政治报的革命脚手架原理建设出工业化组织雏形,并且通过明确的流水线分工协同作战锻炼出言行合一的纪律。在这样的路线下建设出具铁一般纪律、协同工作配合到位的革命组织。届时开启全国一盘棋的融工战略,全国各地同时开展融工来建设地上群众组织。而众所周知,唯有纪律才能诞生出战斗力,而唯有力量才能解决广大受压迫群众的困境,所以革命的力量势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良性循环,能够打造出紧密如石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