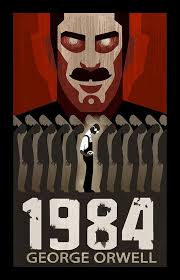广告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 (@maoistQAIIbot) 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编者按:
1.奥威尔就是红皮自由派,这也是托派的本质。托派把所谓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视为核心原则,搞机械的所谓官僚划分。本质上和自由派一样都是对抽象原则的恋物癖,拜物教。于是这种世界观中,只要统治机器力量足够强大,统治方式足够强硬,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无产阶级就会盲目地愚昧地崇拜老大哥。然而事实从来不是如此,被统治阶级从来不是麻木不仁,他们知道需要反抗,但是迫于形势没有办法进行有效反抗,这才形成了看起万马齐喑的场面。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锋队来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2.在奥威尔笔下,似乎一切压迫的根源在于思想,压迫者依靠思想上的垄断来维护统治,无产阶级没有反抗思想于是不反抗,因此自然而然便能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是思想灌输。如今的一批机会主义正是秉着这种唯心思想,认为只需要靠真理便能唤起群众的反抗精神,只需振臂一呼就能发起革命。然而事实是,反动派是依靠强大的物质力量来维护统治,而无产阶级要推翻统治,也必须要有与之相对抗的物质力量,而无产阶级能够依靠的唯一武器只有组织。
《1984》是一部影响颇深的政治寓言小说,作者乔治•奥威尔以大洋国这个虚构国家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如何在极权压迫下失去个体自由与人性。这部政治寓言小说之所以广泛流传,是因为它写在文字中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成为了真实,以至于它简直就是写于1948年的“政治预言”。笔者也曾阅读过这部小说,作者的确在讽刺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可即便如此,这也无法掩饰整个作品的毫无价值,甚至可以说是反动。鲁迅先生曾经说:“……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 ”而《1984》正是如此,它虽被各种群体称为“禁书”(我们在这里且不说它影射的现实对象究竟是谁,是苏联大清洗,还是英国军情五处,还是二者兼有……),可单看其文字与情感倾向中透露出的政治理念,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它最终被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包括中修)接受,以至于成为了反共前线的宣传刊物。
在《1984》中,乔治奥威尔多次谈及大洋国治下的无产者,他们不受“老大哥”和英社党的直接管控,因为他们缺乏反叛意识,只会沉迷于低级娱乐,在沉重的劳役中不可能自觉觉醒去追寻自由。即便如此,奥威尔仍借主人公温斯顿之口说:“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 ,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然而这一切都在故事的结尾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因为故事直到最后,无产者都没有做出任何反抗性的举动,他们沉迷于自己碌碌无为的日子中,仍然自愿承受着权力的压迫,对身旁的不公没有任何反应。在整篇小说里,无产者始终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而存在的,且由于反动派对思想的垄断,又是不可能被动员的。从此处就可以窥探奥威尔对群众的无知偏见。毛主席曾经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铁一般现实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即便这个上层建筑有多么地“完美无缺”,也不可能掩盖群众的怒火,无产阶级的斗争性是意识形态所不能改变的。佳士运动、蒲城事件都展示了群众反对压迫的决心,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许都没有接受过反抗思想的灌输,受着赵国严格的信息管制,但在赵国日复一日的剥削之下,他们也能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压迫,也会在某一时刻揭竿而起进行反抗,因为任何阶级在自己的阶级利益受到侵犯时都是异常敏感的!在对无产阶级形象的认识方面,奥威尔与当下的某些泛左翼是臭味相投的,他们俯瞰着荒原,对无产者平日里的政治冷感和毫无作为着急地直跺脚,心想着:工人们要是有哪怕一丁点斗争性就好了。这些文人的头脑还停留在史诗的理想化叙事当中,哪怕这些人的确参与过斗争(奥威尔参与过国际纵队,泥潭派亲自“到工人中去”,革命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将一部分小资席卷进运动之中),也是不懂得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即便它每时每刻都发生在自己身旁。他们实质上是革命的投机者,就像站在风口上的猪一样,只能顺着革命高潮而上,却不能在革命低潮时真正克服困难,科学分析局势,甚至要反过头来把无产者贬得一文不值,是“连自发斗争都还没开展”。
奥威尔的唯心史观也导致了他对革命、革命家的庸俗理解。在小说中,大洋国的统治者运用权力动员了所有的人力物力,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根除思想上的异端,小说中的核心党员奥勃良在审讯主人公温斯顿时这么说:“你最后投降,要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在杀死他之前也要把他改造成为我们的人。我们不能容许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不论多么隐蔽,多么不发生作用,居然有一个错误思想存在……以前的专制暴政的告诫是‘你干不得’。集权主义的告诫是‘你得干’。我们则是‘你得是’……”大洋国年复一年对外打仗纯粹是为了使生活物资短缺,通过维持贫苦与狂热使得大多数人无法思考。“思想警察”时刻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无意义的“新话”裁剪思想的厚度,“双重思想”保证人们可以接受前后冲突的两种理念……总而言之,因为“老大哥”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革命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秘密积累知识,逐渐扩大启蒙,最后发生无产阶级造反,推翻党。你不看也知道它要这样说。这都是胡说八道……”对于奥威尔来说,革命似乎就是由几个掌握真理的虔诚圣人在群众中布道达成的,而只有这些个圣人会对剥削压迫产生反应,天生就有着自觉觉醒的潜能。主人公温斯顿就是这样理想化的革命圣人,在故事的一开头,他就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洞察力,会对自己深处的社会环境产生质疑,他个人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着自己思想自由的理念,认为这是一种对大洋国的反抗。在故事的结尾,温斯顿这个主角个体被大洋国彻底改造,打心底里对“老大哥”无比热爱,奥威尔在此处更像是把温斯顿描写成了一个殉道者,这个形象实际上影射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在工业化帝国主义时代下的终结。奥威尔原打算将小说命名为《欧洲的最后一个人》,也更加重这种意味。
正是这种自我感动、自我抬高的唯心史观将奥威尔及其笔下的人物带向了悲剧的结尾,而这个过程又要发生在今天的泛左翼身上。这些先生们似乎认为真理本身具备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能够直接把一个政权吓倒、推翻,能够自动地号召起千百万的群众。然而真理本身不转化为物质力量,就必将会一步步地变为僵死的教条,甚至成为过时的谬论。号召群众发起斗争,不能够幻想着通过思想上的启蒙运动达成,革命的意识形态不是凭空产生的,靠一两个洞察力极强、理论水平高超的人得来的,而一定要有其依附的物质基础,要建立在现实的阶级斗争过程当中。先进分子们必须要坚持列宁的政治报路线,在长期的义务劳动中检验自己的革命决心,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巩固自己的先进思想。践行群众路线就必须铭记扫帚哲学,须知群众当中的落后思想根源于落后的雇佣劳动,而负起领导责任的革命家组织要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即能够组织工人们起来从事一种新的义务劳动,它能够锻炼起群众的战斗协同能力,最根本的生产目的是生产出工人们的反抗思想,达成这一点不是靠嘴皮子功夫就能办到的。奥威尔及泛左翼们对这种路线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要求像作文章那样雅致的“革命”,要求苦行僧那样的“革命家”,一旦革命者内部出现了敌我矛盾,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要站在“少数派”那面,还反骂多数的人是蠢材,是掌控权力的独夫,一旦出现“强制”、“纪律”就必然是不好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掌无产阶级之权,专投机分子之政,真正有原则的革命者是不会对权力产生厌恶的,而是会科学分析权力是否维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当前无产者最缺的就是权力,没有权力,真理也会变成谬论,就会落得小说中温斯顿那样可笑的结局。
奥威尔曾说:“我写《1984》是为了警醒世人,不是使用说明书!”可这种警醒在目前看来却是滑稽的,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无产阶级的斗争性需要靠别人赋予,革命理想不能够与实际的权力沾边,无产阶级要靠真理的力量推翻压迫,这简直是自命清高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若是各位同志们真正阅读过原文,就更可以发现小说中对政治现象的理解有多么反科学,其政治寓言的价值是多么地匮乏。整篇小说可以说就是奥威尔这类投机分子未能从革命中获利,反在革命中受到排挤、打击后的满腹牢骚。同为作家,鲁迅却能够一以贯之地在作品中发出光与热,从不把战斗的矛头指向人民群众,这是为什么呢?鲁迅经历过权力的轮换更迭,经历过同一阵营的分裂与背叛,也被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青年人痛击过,可终于还是振作起来,这是因为他始终坚持政治挂帅,心系天下苍生的命运,对现实斗争不抱有任何幻想,也从未在乎过个人的那些利益过失。所以鲁迅至死也不会写出《1984》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这些革命现实主义者相信,铁屋子总是要被砸碎的,哪怕一万年后也是会被砸碎的,而做到这一点,就是要让群众们组织起来形成集体,依靠手中的权力打破剥削社会的历史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