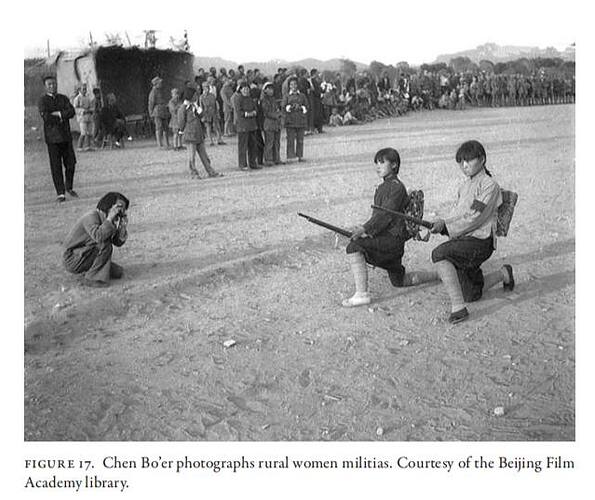编者按:该篇为王政《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的部分翻译,作者所持立场与本站或不完全一致,注意辨别,仅供参考。
一位革命艺术家的形成
陈波儿于1937年8月秘密加入中共。1938年底,党派她去延安,这里被许多思想左倾的年轻人视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孕育新中国的基地。自从她在1937年初看了埃德加·斯诺拍摄的一部关于延安生活的纪录片后,陈就一直渴望去延安。为了完成党的一项特殊任务,陈把她年幼的儿子送到了重庆的一所寄宿学校,独自一人去了延安。
陈波儿要领导一个“战区妇女儿童考察组”,其表面任务是建立战区妇女和后方妇女之间的联系。这六位年轻的共产党妇女在中国北方的战火纷飞的地区旅行了十五个月,收集信息,开展村民教育,并参与当地的抵抗工作。尽管有危险、困难和疲劳,陈还是设法写了几份报告和文章,其中三篇发表在从上海迁至战时首都重庆的《妇女生活》杂志上。这些文字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转型阶段。
在《三位缠足妇女的印象》中,陈波儿以兴奋和敬佩的心情描述了农村妇女“肩负起民族复兴和妇女解放的双重任务”,“高昂着头走出了极端封建的农村家庭”。她关注了三位中年缠足妇女,她们在缠足的情况下领导了当地的抵抗工作。陈用她们在集会上的演讲和她对她们的采访中的长篇引语,即时传达了这些不识字的妇女的声音。她的报告也是一种民族志,记录了当社会制度,包括家庭,被抵抗运动重新组织起来时,农村地区性别规范发生的转变。它证明了中共女权主义者在基层组织工作中坚持民族复兴和妇女解放的“双重任务”的观点,动员并赋予了农村妇女力量。
其中一位缠足妇女领导人张淑凤(Zhang Shufeng)宣称:“抗战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人。……抗战真是太好了。它激发了许多村庄的人性精神。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地位也提高了,因为一个做饭和养孩子的妻子现在也有为国家做事的机会。没有人再叫我老婆子了。他们都叫我主任、主席。”耿汝章(Geng Ruzhang),另一位领导人,告诉陈:“现在华北的妇女都解放了,自由了……你可以看到妇女参与各种活动,在山路上行走,在山岩上攀爬……华北的妇女都走出了茅草屋。”张庆云(Zhang Qingyun),第三位领导人,评论说,妇女救国会所执行的任务“并不逊色于”男人的任务,这“粉碎了那些一直对妇女和姑娘轻视的观点。”
从她独特的女权主义视角,陈波儿传达了农村妇女如何把抵抗活动作为一个突破父权家庭和村庄中性别束缚的绝佳机会,走出来享受以前只属于男人的特权的空间和社会流动性。她们毫不费力地使用“做人”、“妇女解放”、“自由”和“抗战”等术语,显示了她们对一种政治语言的积极拥抱,这种语言融合了五四女权主义和中共版本的民族主义,后者将民族救亡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转变结合起来。她们表达了由中共在农村根据地为战争努力所进行的“妇女工作”所塑造的新主体性。陈用兴奋的散文,不仅描述了这些农村妇女的生活和思想的转变,也描述了她自己的转变。
遇到这些强大、有能力、英勇的农村妇女,她们有着清晰的政治意识,深深地影响了陈,她是在城市精英中长大的,她们习惯性地把下层妇女想象成被动的受害者,等待着受过更好教育的妇女的解放和提升。陈波儿毫不掩饰地欢欣鼓舞,把她的报道变成了一首赞美农村妇女的颂歌。她描述了三位妇女生活中许多感人的片段,就像电影场景一样生动。例如,这些脚小而畸形的妇女在冰冷的泥土路和雪覆盖的山路上行走非常困难。为了参加一个遥远的重要会议,她们一次又一次地跌倒,最后不得不在冻僵的地面上爬行,在雪坡上滚下去,到达目的地时浑身伤痕累累。这些场景深深地刻在陈的心中,以至于她后来在她的《中国女儿》(1949年)中用视觉方式呈现了它们,这是第一部以革命英雄为特色的电影。在她的报告中,她表达了她的钦佩:“确实,这些缠足妇女在艰苦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屈精神,是抗战中最珍贵的诗歌。她们写下了妇女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