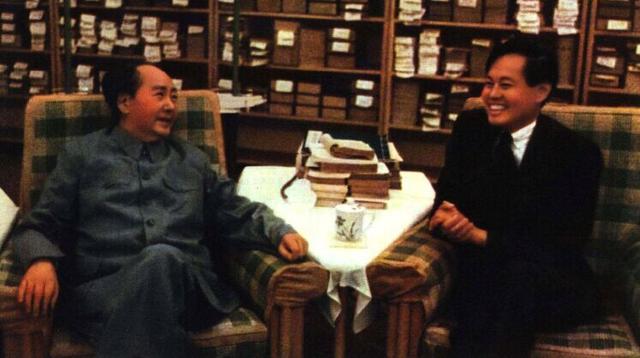毛主席在1965年重读1933年写的《长冈乡调查》时,留下过一段哲学批注:“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如果注意这两个时间点,我们就会发现新与旧不是割裂开来的。老革命会遇到新问题,老问题也会得到新解答。“革命”的共产党会变成“训政”的国民党;主张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宣言,也会演变为信奉驯服工具的共产党修养。
沉舟侧畔千帆过,沉舟与千帆不是割裂的此一时彼一时;病树前头万木春,病树和万木也不是割裂的老一代新一代。毛主席对发动文革说过:“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左派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难道是那个《皇帝的新衣》里的新决议?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主席留下的这个课题,我们如何给他交上一份令他满意的答卷呢?这是我们重新回到这个课题的真正意义。本期《“五十天白色恐怖”之管中窥豹》可以对照佳士运动中声援团的遭遇。蒯大富和声援团面对带引导的“共产党”时,那种窘境不是如出一辙吗?带引导的“共产党”会如何对待群众运动,其逻辑不是完全一样的吗?蒯大富只是给“共产党”的工作组提意见,结果呢?声援团只是抗议“共产党”不像共产党,抗议“答应建工会却出尔反尔”,结果呢?所以毛主席的课题一直没有远离我们,而是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警醒着我们:面对这样的“共产党”,你们该如何斗争?你说你主张共产主义,他说你寻衅滋事;你说你信仰阶级斗争,他说你煽动颠覆;你说他“假共产党”,他说你“犯罪分子”。不要想绕过这个课题,在当代一切革命左翼和全体马列毛主义者都必须直面这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才能产生最大的价值。回避与曲解只是继续制造混淆视听的垃圾而已。
往期《解释与改变》里论证的是检验一个理论的时间跨度很长;《实践是如何检验真理的?》说明检验过程之复杂与曲折;《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多次反复是如何产生的?》说明错误是正确的先导及其根源。这一期里主要探讨一下解题思路:旧课题会有新答案。我们仍然是拿自然科学来举例说明。这个课题是物理学中的原子核β衰变。
我们知道放射性物质的放射现象,放射过程就是原子核衰变的过程。其中一种射线叫做β射线,《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多次反复是如何产生的?》里发现中子的查德威克证明:α射线和γ射线的能谱是分立的,α衰变和γ衰变中发射的粒子所带走的能量正好与原子核初态末态的能量差相等。然而,β射线的能谱却有明显的不同,是连续谱而不是分立谱。也就是说,β衰变放射出来的电子,能量从零到某一个最大值都有分布,可是,原子核的初态和末态能量都是稳定的非常分明的定值。衰变电子的能量竞会小于两态之间的差值。人们感到极为迷惑。那一部分能量到哪里去了?这样就会违背能量守恒。所以玻尔只能解释为有可能能量守恒只是在统计意义上成立,对每一次衰变并不一定成立。泡利不相信在自然界中唯独β衰变过程能量不守恒。他在 1930 年提出中微子:“只有假定在β衰变过程中,伴随每一个电子有一个轻的中性粒子一起被发射出来,使中子和电子的能量之和为常数,才能解释连续β谱。”他还指出:这种中微子的速度不同于光子,质量很轻,穿透力极强,因此很难探测到。
费米接受了泡利的假说,并进一步提出弱相互作用的β衰变理论。他认为,正象光子是在原子或原子核从一个激发态跃迁到另一个激发态时产生的那样,电子和中微子是在β衰变中产生的。他指出,β-衰变的本质是核内一个中子变为质子,β+衰变是一个质子变为中子。中子与质子可以看成是核子的两个不同状态,因此,中子与质子之间的转变相当于一个量子态跃迁到另一量子态,在跃迁过程中同时放出电子和中微子,它们事先并不存在核内,导致产生光子的是电磁相互作用,而导致产生电子和中微子的是一种新的相互作用,费米称之为弱相互作用。当年小居里夫妇发现的放射正电子的人工放射性验证了β+衰变。而费米预言的轨道电子俘获过程的可能性也在1938 年被观察到了。然而直到上世纪 40 年代初,还没有任何实验能够实际观测到中微子的存在。
中微子的性质很独特,它不带电,不能引起电离效应,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所以很难观测到它的踪迹。它很稳定,要观测到必须通过它与物质的相互作用。1938—1939 年间,克兰和哈尔彭从观察到的电子在磁场中的偏转和核反冲的径迹,估算原子核的能量和动量,数据表明在β衰变中存在第三个粒子。我们“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在1942年发表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他分析了克兰和哈尔彭有关β衰变中核反冲的实验后,认为由于反冲原子的电离效应太小,有必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探测中微子。他指出:“当一个β+放射性原子不是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 K 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原子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取决于所放射的中微子,原子核外电子的效应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只要测量反应后原子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比较容易找到所放射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而且,由于没有连续的β射线放射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所有的原子都是相同的。”此后直到1952年,陆续有实验物理学家根据王淦昌方案间接得到了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与他的预期相符。1953 年,雷因斯和柯恩小组利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大型裂变反应堆,设计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实验方案。经过艰苦的工作,他们在 1956 年宣布,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从而打消了关于中微子存在的任何怀疑。
以上中微子的发现过程基本上和中子的发现过程一样漫长而曲折,用来证明前几期的哲学观点也基本适用,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领域不止于此。泡利在β衰变方向提出假说后的几十年里,上个世纪的三十、四十、五十年代,随着加速器的发明与使用,人类对基本粒子的认识越来越丰富,为了描述这些基本粒子的物理过程,能量、动量、质量、电荷这些基本概念有点不够用了,物理学家随后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物理量。宇称及宇称守恒就是这样的新概念。宇称守恒反映了镜像反射的不变性,也即把一个物理过程换成它的镜像过程后仍然遵从原来的规律,体现的是物理规律在空间反演下的对称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实验中发现了质量、寿命和电荷都相同的两种粒子,一个叫θ介子,另一个叫τ介子。这两种粒子唯一的区别在于:θ介子衰变为两个π介子,而τ介子衰变为三个π介子。分析实验结果可以得出:三个π介子的总角动量为零,宇称为负,而两个π介子的总角动量如为零,则其宇称只能为正。鉴于质量、寿命和电荷这三项相同,这两种粒子应是同一种,但从衰变行为来看,如果宇称应守恒,则θ和τ不可能是同一种粒子。
1956 年,杨振宁(34岁)和李政道(30岁)在论文里提出:这一疑难的关键在于人们认为微观粒子在运动过程中宇称必须守恒,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宇称守恒是经过检验的,但在弱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宇称并没有得到判决性的检验,没有根据说它一定守恒。如果在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可以不守恒,则θ-τ疑难将迎刃而解。而且在已有的实验资料里,基本粒子在弱相互作用领域内没有一个例子证明宇称是守恒的。这里面存在一个解题思路的问题。
θ-τ疑难本身就是宇称不守恒最有力的证据,为什么还要找新的方案去验证自己的理论。因为当时粒子物理学还是个杂乱无章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用一个孤证是很难说服人的。关键是要找到那种毫不含糊,具有判决性的实验来证明自己。他们首先想到了β衰变。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精通β衰变实验的同事吴健雄。他们想设置两组含弱相互作用而互为镜象的实验装置,考察这两组装置是否得出相同的结果,如果结果不一样,就可以肯定宇称不守恒。其中β衰变实验吴健雄建议选钴-60,测量极化的钴-60原子核所放射的β粒子(即电子)的角分布,从而检验左右是否对称。结果证明:电子在空间中的分布果然是不对称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理论得到了证实,θ和τ是同一粒子也得到了确认。
题目还是老题目,但是答题的人是后来的新人。用的必须是新办法,放弃的是一些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于是才能找到一片新大陆。这是马列毛主义辩证法永恒的魅力。
( 欲获赠本站精选内容合订本者,可发邮件至 FrankRuthasw678@gmail.com )